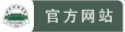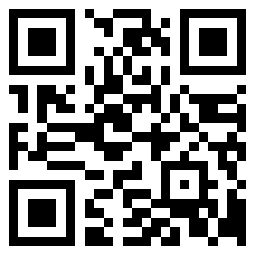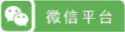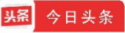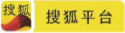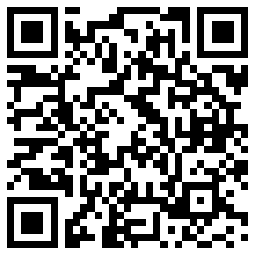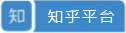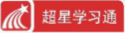2008—2011 Surveillance of Resistance in Bacteria Isolated from Intensive Care Units in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
摘要:目的 了解重症监护病房病原菌分布及其耐药情况。方法 2008年1月至2011年12月间北京协和医院重症监护病房患者中连续分离到3507株非重复细菌, 采用纸片扩散法对临床分离菌株进行药敏试验, 按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研究所2011年标准判读药敏结果, 采用WHONET 5.4软件分析数据。结果 3507株非重复细菌中, 革兰阴性菌占74.7%, 革兰阳性菌占25.3%。10种最常见的细菌分别为:鲍曼不动杆菌(28.1%)、铜绿假单胞菌(12.8%)、金黄色葡萄球菌(10.0%)、大肠埃希菌(7.8%)、肺炎克雷伯菌(7.7%)、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7.1%)、嗜麦芽窄食单胞菌(5.2%)、屎肠球菌(4.4%)、阴沟肠杆菌(2.3%)、粪肠球菌(2.3%)。4年中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MRSA)和耐甲氧西林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methicillin-resistant coagulasenegative staphylococci, MRCNS)的总检出率分别为74.9%(262/350)和83.4%(206/247), MRSA中有82.6%的菌株对磺胺甲噁唑-甲氧苄啶敏感, MRCNS中有79.6%的菌株对利福平敏感。均未发现对万古霉素、替考拉宁和利奈唑胺耐药的菌株。粪肠球菌对氨苄西林(18.2%)、呋喃妥因(5.6%)和磷霉素(2.7%)的耐药率较低, 屎肠球菌对万古霉素和替考拉宁的耐药率分别为9.5%和7.5%, 粪肠球菌对二者的耐药率分别为1.3%和1.3%。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的总检出率分别为60.2%(165/274)和46.8%(126/269)。鲍曼不动杆菌泛耐药株(除外米诺环素)的总检出率为60.4%(596/987), 铜绿假单胞菌泛耐药株的总检出率为5.6%(25/450)。鲍曼不动杆菌对亚胺培南和美罗培南的耐药率分别为82.8%和83.8%, 对米诺环素的敏感率为58.0%。铜绿假单胞菌对阿米卡星的耐药率最低, 为16.8%, 对亚胺培南和美罗培南的耐药率分别为42.6%和35.3%。结论 在重症监护病房, 碳青霉烯类抗生素对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仍保持高活性, 鲍曼不动杆菌耐药性呈增长趋势, 特别是多重耐药和泛耐药菌株。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ates of resistance in bacteria obtained from intensive care units (ICU) in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Methods A total of 3507 non-duplicate clinical isolates from ICU were collected from January 2008 to December 2011. Disc diffusion test (Kirby-Bauer method) was employed to study the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The data were analyzed by WHONET 5.4 software according to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Standards Institute (CLSI) 2011 breakpoints.Results Among these 3507 non-duplicate clinical isolates, gram-negative organisms and gram-positive cocci accounted for 74.7% and 25.3%, respectively. The 10 most common pathogens in ICU were A. baumannii (28.1%), P. aeruginosa (12.8%), S. aureus (10.0%), E. coli (7.8%), K. pneumoniae (7.7%), coagulase-negative staphylococci (7.1%), S. maltophilia (5.2%), E. faecium (4.4%), E. cloacae (2.3%), and E. faecalis (2.3%).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MRSA) strains and coagulase-negative staphylococci (MRCNS) accounted for 74.9% (262/350) and 83.4% (206/247), respectively. However, 82.6% of MRSA strains were still susceptible to trimethoprim-sulfamethoxazole, while 79.6% of MRCNS strains were susceptible to rifampin. No staphylococcal strain was resistant to vancomycin, teicoplanin, or linezolid. The resistance rates of faecalis to ampicillin (18.2%), nitrofurantoin (5.6%), and fosfomycin (2.7%) were low. The resistant rates of E. faecium and E. faecalis to vancomycin were 9.5% and 1.3%, while to teicoplanin were 7.5% and 1.3%, respectively. Extended spectrum β-lactamases (ESBLs) -producing strains accounted for 60.2% (165/274) and 46.8% (126/269) in E. coli and K. pneumoniae, respectively. The rates of pan-resistant (except minocycline) A. baumannii and P. aeruginosa were 60.4% (596/987) and 5.6% (25/450). The resistance rates of A. baumannii to imipenem and meropenem were 82.8% and 83.8%, respectively. The susceptible rate to minocycline was 58.0%. The resistance rates of P. aeruginosa to imipenem and meropenem were 42.6% and 35.3%, respectively. P. aeruginosa isolates showed the lowest resistant rate (16.8%) to amikacin.Conclusion Carbapenems remain highly active against E. coli and K. pneumoniae. The antibiotic resistance of A. baumanii is increasing, especially those multidrug-resistant and pandrug-resistant strains.
-
孕妇健康作为公共卫生内容之一,日益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近年来,中国随着生育政策放开、人口老龄化、慢性疾病增加和社会经济发展,产科的服务能力凸显不足,医护人员工作压力加大。国家卫生计生委指出了在“互联网+”时代移动医疗的发展方向。随着信息化、数字化、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与便携式、可穿戴式设备的综合应用,移动医疗正逐步走向医院和家庭。这为解决健康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提供了新的手段。
可穿戴移动医疗设备在临床上早已广泛使用,比如常见的心电图仪、血压计、血氧仪等均可携带,检测后使用计算机读取数据并进行分析。此类设备可称为信息化和数字化时代的第一代可穿戴医疗设备,其专业性毋容置疑,在临床发挥着巨大的医用价值,但其舒适性和易用性较差。从医学角度看,可穿戴医疗设备的优点具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某些特定专业设备的智能化、可穿戴化及便携化,可低成本监测脆弱人群(如孕妇或老人)自身健康与疾病状态,从而减少经济及时间成本。如可穿戴医疗设备不仅为具有心脏病史或妊娠合并心脏病的孕妇节省了检查费用,同时减少孕妇路程往返风险,从而提高监护质量,改善就医体验;(2)慢性疾病患者通过可穿戴设备可累积长期健康数据,避免传统疾病日记的不良依从性[1]。
随着智能移动终端设备的普及和互联网、物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可穿戴移动医疗设备在妇幼健康领域应用也越来越广,同时加速了智慧妇幼时代的到来[2]。对比传统孕妇监测设备,可穿戴设备突破了传统生理参数采集与医疗监护模式,可对孕妇的生命体征数据进行实时动态管理。孕妇通过可穿戴移动医疗设备,可自主监测胎心、血糖、血压、体重、脉搏、血氧、血脂、心电、尿液等项目。
孕妇可穿戴医疗设备是为孕妇设计的具有临床健康监护用途的随身配件。这种以配件为存在形式的新型医疗设备,融合了先进材料、传感、电路设计、信息传输和处理等前沿技术,在实现监护功能的同时给孕妇提供舒适便捷的使用体验。孕妇可穿戴技术的出现以及在医院中的应用与管理,不仅弥补了传统孕妇监护设备无法长时间、连续、动态监测的弊端,而且颠覆了传统孕妇健康监护管理模式。
1. 孕妇可穿戴设备及关键技术
1.1 孕妇可穿戴设备
目前,国内外各种孕妇可穿戴设备种类繁多,可对孕妇体重、血压、血糖、血氧、体温、胎心等生理参数进行随时随地监测与管理,解决了孕妇监护不便的问题[3]。李天魁等[4]研究了集成远程胎儿监护功能托腹带,结合手机软件实时显示,解决了围产期孕妇腰椎过度前凸导致的腰背疼痛、肌肉疲劳等健康问题。为了满足长期连续胎儿监控要求,李思君等[5]实现了基于微处理器的低功耗可穿戴式胎心音测量设备,较目前常用的单通道多普勒超声胎儿心动测量技术,可获得更加全面的监测数据。Fanelli等[6-7]通过可穿戴的硬件设备采集提取胎心率数据并传输至医院设备,医生分析结果后给出反馈,实现了家用胎心率的远程监控,使胎儿监护更加便捷和廉价。Hiyama等[8]研究了一种基于密集人群场景的可穿戴式胎儿保险杠,通过测量外界对孕妇腹部的推力来预测胎儿可能受到的危险。一种新型的正力测量传感器架构有效改善了测量精度和防止抖动干扰,实现了可穿戴式的宫缩检测[9]。美国Bloomlife公司研发了一款妊娠晚期可穿戴设备Belli,能够监测跟踪孕妇胎动等统计数据并即时发送到智能手机APP上[10]。
1.2 孕妇可穿戴设备的关键技术
新型材料、高性能传感器、低功耗电池以及安全有效的无线传输技术是孕妇可穿戴设备的关键技术,推动着孕妇可穿戴设备不断更新发展。
1.2.1 可穿戴材料
可穿戴设备需直接佩戴在孕妇身上,并覆盖在高度柔展的皮肤表面。对孕妇来说,可穿戴设备的舒适性、轻便性、耐用性和灵活性非常重要。基于纤维结构的材料非常理想,同时,新型导体和半导体材料的发展为孕妇可穿戴设备的设计提供了新的动力,例如导电高分子聚合物、金属和金属氧化物的纳米粒子、碳基纳米材料等[11-12],在具有良好导电性的同时,又具有很好的机械特性。导电织物具有柔软、轻薄、易拉伸变形的特点[13],非常适合于孕妇穿戴。
1.2.2 传感器
穿戴式设备监测孕妇获得的各种生理参数和体征信号均需依靠强大的生物传感技术[14]。因此,高灵敏抗噪的柔性传感器设计是孕妇可穿戴设备的核心之一。随着材料和电子技术的进步,可穿戴生物传感器性能逐渐升级。较为常见的传感器包括监测心电的导电织物、监测脉搏和血氧的光电传感指环、监测呼吸的压电腰带和胸带、监测体温的红外线耳环等[15]。可穿戴传感器向着功能更多、信号更稳定和功耗更低方向不断发展。
1.2.3 电池
任何可穿戴设备均离不开电池,相比快速创新的孕妇可穿戴设备,可穿戴电池的发展速度则比较缓慢。尽管绝大多数可穿戴设备使用了蓝牙低能耗技术,但孕妇依然需频繁充电来确保设备电量充足。根据目前市场上各种可穿戴设备的使用情况,主要有以下几种电池技术:能量收集、锂离子电池、薄膜电池、石墨烯电池。各种电池技术均有不同优点和缺点[16]。超低功耗、高密度聚合物电池的使用,能够保证设备最大续航时间和最小体积及重量。而为了满足孕妇对舒适性的要求,柔性电池是当前研究的重点[12],以满足便携式和可穿戴的需求。
1.2.4 无线数据传输
可穿戴设备可采集到海量孕妇生理数据[14],同时,孕妇对舒适性与便携性的需求使其体积趋于小型化。因此,需将可穿戴终端采集的数据上传至智能手机或计算机等处理器或移动互联网云平台进行计算,计算结果再传至可穿戴终端反馈给孕妇,而高效安全的无线传输技术则是这种应用模式的保证[17]。目前使用较广泛的无线通信技术主要包括Wi-Fi、蓝牙、ZigBee、红外线等,其中,蓝牙和ZigBee常被用作孕妇可穿戴设备的数据传输方式,其优点是低功耗、低成本。
2. 孕妇可穿戴设备的应用
20世纪90年代孕妇可穿戴设备已在欧美各大医院得到普及,到2010年后逐步呈现走出医院、走向家庭,更多面向个人提供定向、个性服务发展的特点,并与智能移动终端和物联网技术发展紧密同步,同时与大数据和云计算结合起来,使妇幼保健从救治发展到预防阶段。例如,英国牛津大学采用移动胎儿监护仪可提高围产期保健质量,其能同时远程监护多名孕妇[18];美国Mercy医疗中心孕产妇和胎儿健康中心采用远程胎儿监护系统进行医生远程会诊、医患远程咨询[19];希腊约阿尼纳大学开发母胎健康多参数远程监护仪,可监护孕妇和胎儿的心电、血压、温度等数据[20]。
我国人口数量大,医疗资源相对缺乏,医疗配置不够合理。此外,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高龄与高危孕妇健康问题也日益突出。因此,构建一种新型孕妇健康应用模式,让有限的妇产科医疗资源达到最优化配置,让尽可能多的孕妇享受专业医疗指导和服务,成为全社会的共同愿望。二孩政策放开以来,全国进入了生育高峰期,医院产科爆满,而因场地所限,医院能够容纳的产检孕妇数量有限。孕妇在医院排队进行常规产检,仅胎心监测一项就需要约50 min,而采用可穿戴式胎儿心电设备在家进行监护,不仅节省了时间,还能够随时进行监测,有效降低了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率[21-22]。
对于妊娠合并高危因素[23-24],如妊娠合并糖尿病、高龄产妇贫血、妊娠期高血压、前置胎盘、巨大胎儿、多胎妊娠等,妇产科医生可在妊娠28周后建议孕妇使用可穿戴式胎心仪,在家进行自我监护,从而进行密切的动态监测,然后上传胎心监护图[25]。如图 1所示,医生可随时在移动智能终端APP查看胎心监测数据,并进行判读和针对性指导。另外,对于那些进行过不孕症治疗采用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受孕、高龄、较为焦虑的孕妇,也可使用可穿戴式远程胎心仪在家监护并上传胎心图,让医护人员及时了解胎儿的当前情况。
通过可穿戴智能设备,医生可持续跟踪孕妇围产期健康情况和产后康复进展情况,及时发现潜在的风险因素。可穿戴智能设备还可动态评价药物疗效,例如可穿戴式母胎心电设备能够评估孕妇心律失常药物的疗效;针对妊娠期糖尿病,采用可穿戴无创血糖仪进行血糖监控;有些疾病加重概率高,如妊娠合并心脏病,所以孕妇需要实时监护心力衰竭以避免病情突变。
3. 我国孕妇可穿戴设备的管理
合理的孕妇可穿戴设备的管理,能够避免孕妇就医和住院治疗的次数,大大节约费用和人力成本。孕妇可穿戴设备的管理不仅依赖软硬件技术,更需要移动医疗和远程监护以及合理医疗管理模式的支撑。我国妇幼领域的医疗模式与国外不同,主要有两种管理模式:(1)设备制造及运营企业与医院直接合作;(2)企业建设自己的远程医疗中心。孕妇可穿戴设备的出现正在慢慢带动妇幼医疗健康行业的转型,同时也对现有的医疗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虽然孕妇可随时随地采集自身数据,但与院内监测的数据在精度上有很大不同。此外,由于其行业内部标准滞后于技术发展,相应法律、法规的建立也比较滞后。
基于孕妇可穿戴设备的远程监护管理流程如图 2所示。通过网络信息技术将胎心、血氧、血糖、血压等重要指标数据进行收集并传递到监护中心进行分析,帮助医院进行宫内胎儿生存状况综合判断。这样,医生可及时了解胎儿在整个妊娠期的生长发育情况,并给予孕妇相应的健康建议,及时预测、预防并处理影响胎儿的各种不良因素,如缺氧、宫内窘迫等。
胎心远程监护的典型应用与管理场景为通过连接可穿戴智能多普勒胎心仪,利用移动互联网,结合物联网技术,实现医院、医生和孕妇三大主体在数据基础上的实时无缝对接,可将医院胎心监测服务延伸至院外,显著提升医院的围产期健康管理水平,降低孕产妇死亡率。通过智能手机移动APP应用和信息管理平台实现孕妇与医生的互动交流。通过数据挖掘与分析及专业医生的判读与指导,实现自我健康管理。更重要的是,孕妇可穿戴设备的应用可及时发现孕妇健康隐患和高危因素,利于医院及早进行干预。
医院妇产科引入基于可穿戴设备的健康监护管理模式可实现对孕妇生命体征数据的动态实时管理,加强围产期监测,优化孕期质量,降低医院门诊产检压力,缓解产科医生工作强度[26-27]。通过“可穿戴设备物联网化+医院信息系统+互联网”打造全新的智慧妇幼管理模式,为医院与医院、医生与医生、医生与孕妇、医生与智能医疗器械、孕妇与智能医疗器械之间建立沟通桥梁,打通信息孤岛,优化就医流程,改善就医环境,提升医患满意度,为医护人员、医院管理者、卫生主管机构人员提供专业、高效的管理工具。
4. 存在问题
在孕妇可穿戴设备领域,通常认为设备监测的孕妇生理参数数据准确性是最大的问题,但设备管理方面的其他问题同样不容忽视。
4.1 设备管理尚未与现有医疗模式结合
目前管理的主要问题是无法通过电子医疗档案结合孕妇可穿戴设备建立并扩展新的管理模式。从医院角度,希望可查询、调用以不同组织方式呈现的记录;从妇幼保健管理角度,希望可建立不同孕妇健康管理平台的子系统。另外,孕妇可穿戴设备必须与现有医疗模式有机结合,仅提供单纯的数据采集功能很难激励孕妇和医生持续参与。只有应用于主流临床流程,使之成为能有效提供医疗服务模式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人工智能算法的处理分析或由产科医疗人员进一步提供深入解读,为孕妇反馈有临床意义的信息并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才是可穿戴设备实践应用能获得持续发展和广泛接受的关键。
4.2 体积大且配置与操作复杂
目前的可穿戴设备对于孕妇来说,远远不够小巧、轻便、美观、精致。无论是Monica母胎心率记录仪,还是三瑞SRF系列多普勒胎心仪,易穿戴性与易携带性均有待提高,且这些设备需由妇产科专家或医护人员指导或帮助进行佩戴;而轻便、安装与配置简便、佩戴舒适才是孕妇群体真正需求的。
4.3 电池续航时间短
电池续航问题对于孕妇可穿戴设备而言始终是痛点,由于长时间连续生物信息采集与监测功耗很大,电池容量有限,续航能力也较差, 影响了孕妇对可穿戴设备的使用。当前电池的密度无法通过其他技术手段改变,所以当前主要的解决方法是通过电源管理等技术来节省传感器和处理器的耗电量。同时,一些新电池技术的创新,比如无线充电和快速充电技术也逐渐被应用于可穿戴设备。
4.4 数据采集准确性差
在可穿戴设备使用较多的健康医疗领域,孕妇自行检测的最大问题是无法排斥意外因素带来的数据干扰,比如运动、情绪、服药、睡眠状况甚至天气异常变化带来的影响。此外,目前还缺乏专业的病理分析。可穿戴设备实现数据采集只是健康状况判断的第一步,由于缺乏云端专业的病理诊断和个性化处置方案,因此无法督促孕妇重视数据,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和规律。对于可穿戴设备用于医疗监控,国家相关机构尚未给予明确规范与监管,导致可穿戴设备监测的数据缺乏标准化。因缺乏相应的规范制约,医院对这些数据并不完全认同,导致数据毫无使用价值。
4.5 指标单一
当前市场上,大部分孕妇可穿戴设备只能监测单一的生理数据,无法体现孕妇身体的其他健康指标,因此医生无法对孕妇身体状况作出准确判断。通过围产期多指标孕妇远程监测设备对孕妇的生理信号进行采集,包括胎心、胎动、宫缩、血糖、血压、血氧等指标,可以克服指标单一的问题,从而实现对孕妇进行全围产周期的实时管理。
4.6 个人隐私问题
可穿戴设备可记录的数据量越大、可获得的个人隐私越多,信息安全隐患就越大[28-29]。换句话说,如果孕妇使用这种可穿戴设备时间越久,关于孕妇个人一切信息将无处遁形,包括健康情况和生活偏好等,随时都可能被泄漏。
5. 展望
孕妇可穿戴设备及随之兴起的移动医疗模式可能为未来医疗模式带来巨大变革。各种可穿戴设备结合相应的健康管理系统,可自然、方便、实时记录孕妇自身各项生理参数,为孕妇健康管理和医学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孕妇可穿戴设备的未来发展可概括为如下几个主要方向。
5.1 互联网+
目前的孕妇可穿戴设备是移动互联网下的一个健康管理入口,并搭建基于可穿戴设备的孕妇垂直应用平台。通过接入互联网的可穿戴设备,孕妇可随时随地监测生理数据,并远程上传至医生端,这将彻底改变孕妇的生活方式和医院对孕妇的监护模式。
5.2 提供实时自动辅助诊断
目前,各种孕妇可穿戴健康监测设备的主要功能集中于实现孕妇生理健康指标变化的实时监测,实际上多数都是在扮演浅层的健康管理功能,与真正意义上的诊断及医疗概念相距甚远。因此,有助评价诊断的孕妇可穿戴设备是未来发展的重点,目标是实现实时动态分析与数据可视化,从而减少再入院率。
5.3 大数据挖掘
数据融合、信息整合以及大数据挖掘几乎是孕妇可穿戴设备对孕妇生理参数数据采集和管理领域未被探索的方向。为了为孕妇远程监护提供更好的预测性能和更准确的决策支持,需将不同的监测方式和设备进行整合,并引入自动分析系统,从而提高母儿监护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5.4 整合与细分趋势并存
随着针对孕妇可穿戴设备市场的蓬勃发展,产品类型将呈现整合与细分并行的发展趋势。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可穿戴设备的局限性将会得到进一部解决。设备的功能将越来越完善,专属应用会越来越丰富,价格将变得越来越低廉。
总之,在妇幼保健领域,孕妇可穿戴设备已逐渐从基础研究走向实际应用。基于孕妇可穿戴设备的新型医疗监护模式能实现对生命体征数据的动态实时管理,提高产科医护人员的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从而提升医院的医疗质量管理水平。
-
表 1 2008—2011年北京协和医院重症监护病房菌种分布
菌种 菌株数 构成比(%) 革兰阴性菌 鲍曼不动杆菌 987 37.7 铜绿假单胞菌 450 17. 2 大肠埃希菌 274 10. 4 肺炎克雷伯菌 269 10. 3 嗜麦芽窄食单胞菌 181 6. 9 阴沟肠杆菌 81 3.1 奇异变形杆菌 43 1. 6 黏质沙雷菌 36 1. 4 产酸克雷伯菌 35 1. 3 其他 264 10. 1 总计 2620 100 革兰阳性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350 39. 4 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207 23. 3 屎肠球菌 154 17. 4 粪肠球菌 80 9. 0 鹑鸡肠球菌 22 2. 5 肺炎链球菌 14 1. 6 草绿色链球菌† 12 1. 4 其他 48 5. 4 总计 887 100 *从血液、脑脊液和其他无菌体液分离; †从血液和其他无菌体液分离 表 2 2008—2011年葡萄球菌对抗菌药物的耐药率和敏感率(%)
抗菌药物 MSSA (n = 88) MRSA (n = 262) MSCNS (n = 41) MRCNS (n = 206) 耐药率 敏感率 耐药率 敏感率 耐药率 敏感率 耐药率 敏感率 青霉素 86. 5 13. 5 100 0 65. 5 34. 5 100 0 苯唑西林 0 100 100 0 0 100 100 0 庆大霉素 28. 2 71. 8 92. 6 7. 4 7. 1 89. 3 61. 4 34. 9 环丙沙星 12. 8 87. 2 97. 2 1. 9 6. 7 93. 3 74. 2 22. 6 左氧氟沙星 8 92. 0 97. 4 1. 9 7. 7 76. 9 77. 1 17. 6 红霉素 56. 5 38. 8 91. 4 7. 4 48. 3 48. 3 92. 7 6. 8 万古霉素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利奈唑胺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替考拉宁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磺胺甲噁唑-甲氧苄啶 22. 4 76. 5 12. 0 82. 6 27. 6 69. 0 67. 7 31. 2 克林霉素 33. 3 64. 3 87. 6 12. 4 3. 4 89. 7 60. 4 35. 4 利福平 4. 7 95. 3 78. 8 21. 2 0 100 19. 9 79. 6 MSSA:甲氧西林敏感金黄色葡萄球菌; MRSA: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MSCNS:甲氧西林敏感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MRCNS:耐甲氧西林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表 3 2008—2011年屎肠球菌和粪肠球菌对抗菌药物的耐药率和敏感率(%)
抗菌药物 屎肠球菌(n = 154) 粪肠球菌(n = 80) 耐药率 敏感率 耐药率 敏感率 青霉素 90. 8 3. 3 27. 8 68. 4 氨苄西林 93. 1 6. 9 18. 2 81. 8 高浓度庆大霉素 69. 5 30. 5 53. 9 44. 7 环丙沙星 92. 6 4. 7 60. 3 20. 5 红霉素 93. 2 5. 5 85. 7 2. 6 万古霉素 9. 5 90. 5 1. 3 98. 7 利奈唑胺 0 100 0 100 替考拉宁 7. 5 91. 2 1. 3 98. 7 氯霉素 4. 4 85. 3 39. 7 52. 1 磷霉素 23. 4 43. 0 2. 7 89. 0 呋喃妥因 52. 7 38. 2 5. 6 92. 6 利福平 89. 8 5. 1 51. 3 26. 3 表 4 2008—2011年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对抗菌药物的耐药率(%)
抗菌药物 大肠埃希菌 肺炎克雷伯菌 ESBLs (+) (n = 165) ESBLs (-) (n = 109) ESBLs (+) (n = 126) ESBLs (-) (n = 143) 哌拉西林 100 62. 7 100 41. 7 氨苄西林-舒巴坦 61. 5 35. 3 79. 5 35. 3 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6 4. 2 29. 5 17. 3 头孢哌酮-舒巴坦 13. 1 5. 2 21. 2 10. 7 头孢呋辛 100 40. 2 97. 9 33. 8 亚胺培南 1. 5 2. 5 4. 8 6. 6 美罗培南 0. 5 2. 5 4. 1 6. 6 厄他培南 2.7 3.8 11.4 10.2 头孢他啶 100 37. 8 97. 3 25. 8 头孢噻肟 100 37. 8 97. 3 25. 8 头孢吡肟 100 36. 8 97. 3 25. 3 氨曲南 100 37. 8 97. 3 24. 8 庆大霉素 63. 8 52. 9 71. 6 24. 7 阿米卡星 11. 5 10. 2 20. 9 9. 3 环丙沙星 84. 5 72. 3 58. 5 33. 1 磺胺甲噁唑-甲氧苄啶 79. 8 75. 7 82. 8 33. 3 米诺环素 35. 5 26. 9 54. 4 20. 0 ESBLs:超广谱β-内酰胺酶 表 5 2008—2011年不发酵糖菌对抗菌药物的耐药率和敏感率(%)
抗菌药物 鲍曼不动杆菌(n = 987) 铜绿假单胞菌(n = 450) 嗜麦芽窄食单胞菌(n = 181) 耐药率 敏感率 耐药率 敏感率 耐药率 敏感率 氨苄西林-舒巴坦 84. 3 10. 3 替卡西林-克拉维酸 89. 6 8. 1 49. 7 50. 3 哌拉西林 92. 5 5. 5 38. 8 61. 2 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89. 2 8. 1 30. 6 69. 4 头孢哌酮 37. 7 48. 7 头孢哌酮-舒巴坦 59. 7 14. 9 21. 9 59. 2 亚胺培南 82. 8 16. 8 42. 6 54. 2 美罗培南 83. 8 15. 2 35. 3 60. 3 氨曲南 31. 2 48. 5 头孢他啶 87. 5 12. 0 21. 8 71. 7 头孢吡肟 88. 7 8. 7 23. 3 67. 4 庆大霉素 90. 1 9. 4 20.9 67. 1 阿米卡星 85. 2 13.9 16.8 67. 1 环丙沙星 91.3 8.4 26.9 68. 4 左氧氟沙星 83.5 9.8 33.3 61.2 12.2 86.1 磺胺甲噁唑-甲氧苄啶 91.3 8.1 13.3 86.7 米诺环 20.7 58.0 1.1 98.3 -
[1]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Standards Institute (CLSI). M100-S21, Performance standards for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testing[S]. Wayne: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Standards Institute, 2011.
[2] 张丽, 杨文航, 肖盟, 等. 2010年卫生部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网报告:ICU来源细菌耐药监测[J].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 2012, 22:34-38. http://www.cqvip.com/QK/98445X/20121/40557741.html [3] 朱德妹, 汪复, 胡付品, 等. 2010年中国CHINET细菌耐药性监测[J].中国感染与化疗杂志, 2011, 11:321-329.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zgkgrhlzz201105001 [4] Sanchez Garcia M, De la Torre MA, Morales G, et al. Clinical outbreak of linezolid-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in an intensive care unit[J]. JAMA, 2010, 303:2260-2264. DOI: 10.1001/jama.2010.757
[5] van Duijn PJ, Dautzenberg MJ, Oostdijk EA. Recent trends in antibiotic resistance in European ICUs[J]. Curr Opin Crit Care, 2011, 17:658-665. DOI: 10.1097/MCC.0b013e32834c9d87
[6] Cuzon G, Naas T, Demachy MC, et al. Plasmid-mediated carbapenem-hydrolyzing beta-lactamase KPC-2 in Klebsiella pneumoniae isolate from Greece[J]. Antimicrob Agents Chemother, 2008, 52:796-797. DOI: 10.1128/AAC.01180-07
[7] 杨青, 邹燕萍, 单志明, 等.联合使用抗菌药物对产KPC-2酶肺炎克雷伯菌的影响[J].中华检验医学杂志, 2011, 34:984-987.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zhyxjy201111006 [8] 王艳艳, 刘红, 杜昕, 等.泛耐药肺炎克雷伯菌株的医院内流行特性的研究[J].中华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杂志, 2011, 31:208-212.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zhwswxhmyx201103004 [9] 习慧明, 徐英春, 朱德妹, 等. 2010年中国CHINET鲍曼不动杆菌耐药性监测[J].中国感染与化疗杂志, 2012, 12:98-104.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zgkgrhlzz201202004 [10] 伍育旗, 单红卫, 赵贤瑜, 等.重症监护病房鲍曼不动杆菌医院感染病例对照研究[J].中国感染与化疗杂志, 2010, 10:373-375.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zgkgrhlzz201005011 [11] 谢红梅, 胡必杰, 陶黎黎, 等.重症监护病房环境与临床分离耐碳青霉烯类鲍曼不动杆菌的REP-PCR分型研究[J].中华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杂志, 2011, 31:903-906.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zhwswxhmyx201110011 [12] 周华, 杜小幸, 杨青, 等.亚胺培南耐药鲍曼不动杆菌碳青霉烯酶和16S rRNA甲基化酶研究[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09, 30:269-272.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zhlxbx200903015 [13] Robledo IE, Aquino EE, Santé MI, et al. Detection of KPC in Acinetobacter spp. in Puerto Rico[J]. Antimicmb Agents Chemother, 2010, 54:1354-1357. DOI: 10.1128/AAC.00899-09
-
期刊类型引用(0)
其他类型引用(2)
计量
- 文章访问数: 176
- HTML全文浏览量: 54
- PDF下载量: 8
- 被引次数: 2

 作者投稿
作者投稿 专家审稿
专家审稿 编辑办公
编辑办公 邮件订阅
邮件订阅 RSS
RSS


 下载:
下载: